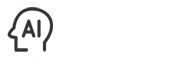王东岳《知鱼之乐》7.惟求存在与通权达变
存在之为存在,这个永远令人迷惑的问题,自古被追问,今日仍在追问,将来还会永远追问下去。——亚里士多德
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老子
难道人,难道诸多民族只是胡乱跌进这大千世界而到头来又将被甩出去?抑或并非如此,我们非得问个清楚不可。——海德格尔
宇宙有没有任何统一性或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律?或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罗素
人是很花哨的,这大概与他本身就是一朵在物演进程上绽放开来的娇柔之花有关。在诗人看来,花是艳丽和芬芳的化身,然而花自己绝不敢有那些多余的浪漫情怀,它的色彩和香气只是为了引诱昆虫来帮它授粉传代,而不是为了给人类装点世界,所以它长满了棘刺以拒绝你的欣赏和伤害。人有时还没有花儿清醒,他常常搞不明白自身禀赋的实际用场和发生根源,居然自己欣赏自己,然后接着糟蹋自己。
譬如,对于任何动物来说,味觉都不过是一种能源指示器,你品尝某物香甜,大多是由于你的机体正需要或缺乏其中的营养素;反之,你品尝某物苦涩,大多是由于它含有可能危害于你的毒素;不是那东西本身就具有或苦或甜的天然味素,而是你的感觉器官必须把它分辨为或弃或取的选择对象。换言之,你的味觉设计并不是为了让你探求物本身的性质,而只是为了达到对你自身生存的维护。所以,但凡是既无益也无害的东西,例如木头,你咀嚼起来就无苦无香,只觉得乏味;也所以,面对同一污物,你虽避之唯恐不远,但苍蝇一定认为它才是真正的美味儿;显然,不是对象发生了变化,而是你和苍蝇的生理需求及感官构造有所不同使然。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他深通上面所说的道理,因此从不主张病人忌口,反而鼓励病人去吃任何自己想吃的东西,甚至当病人苦难当时,就索性让病人在他面前放声嚎啕,因为哭泣也同样不过是一种生理保护机制罢了。回头再来看人类现在造出的种种味素和香精,它虽然可能调香了你的舌头和鼻子,但却遮蔽了你的天赋判别能力。或许,那香味底下所掩盖的,正是你原本需要逃避的某种损害也是说不定。
人毕竟只是一种动物,动物的任何品质都具有特定的求存意义,而且唯其有利于求存,这些品质才能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被保留或发扬,尽管高尚的人类总想对这些生物禀赋给出某种道德等级的划分,其矫情之状足以令鼠辈作呕。早年有人观察到,老鼠遭遇蛇袭,总是立刻吓得呆若木鸡,一动不动的等待它的天敌拿自己来饱餐一顿,于是鄙夷之情油然而生,“胆小如鼠”的贬语中外通行。以后生物学家发现,凡是呆立不动的老鼠大多有望偷生,反倒是落荒而逃的老鼠一定被蛇吞噬。原来蛇的视力极差,昏暗中巍然屹立的鼠身俨如一尊僵石,再笨的蛇也不肯冒险用自己的唇齿去碰壁,蛇会在那里等候片刻,静观那尊石影是否窜逃,逃则影动,一嘴之劳,斩获不菲。就这样,遇蛇奔命的勇鼠基因逐渐被淘汰无疑,只让那些被吓得半死的怯鼠之孽种广布于天下。可以想见,倘若鼠群中偶然也冒出一两个屈原李白似得骚客诗仙,说它们遇险不惊,沉着如山,接着还要指责那些勇于转移的鼠中鬼雄全都是鲁莽的懦夫,因为它们的无辜送命虽属活该,自当予以严厉的申斥。再后来,就连我们那位机智过人的著名侦探波洛先生,想必也不敢忘记鼠辈们的逃生策略和道德评价,当他在尼罗河的游船上险遇毒蛇时,照例只向同行的助手发出救援信号,静等别人前来助战,自己是绝不肯遵循人间的说教和误导而逞一时之勇了。
世间万物,各有千秋,或者说,各有不同的属性代偿,但任何属性都只是为了达到载体的求存,并且都只是由于不得已才变通缔造出这种代偿产物。动物的智能也不例外。让我们先来看看作为智能之基础的神经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单细胞生物依靠自身广大的细胞膜来与外界发生物质和信息的交流,之所以说它“广大”,乃是由于任何物体,如果把它分割的越细,则其单位体积所占有的表面积值就愈大,若以人体的“面积/体积”比值为一,则像大肠杆菌那样的单细胞就达30万左右。这样一个小体积、大面积系统自然特别有利于细胞内外之间的代谢沟通,细胞膜上微孔斑斑,通透性很强,这相当于它们浑身上下长满了通天的嘴和眼,所以单细胞生物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单细胞原生动物(如变形虫)一旦进化成多孔动物(如海绵)或腔肠动物(如水螅),多细胞之间的聚合随即导致细胞膜遮蔽,好在此刻的细胞排列还只有两层(双胚层),各细胞的部分质膜尚可暴露于孔隙或腔管中,因此尽管全体细胞已不能不使自己有所变形,但神经系统暂且可以不必赘生;等到再进化一步,变成扁形动物(如涡虫),细胞的聚集发展到三层以上(三胚层),相当一部分细胞就被彻底封死,至此则各细胞的分工必须细化,不同的生物组织由以创立,为了协调各细胞各组织之间的营养配置和功能配合,有些细胞只好演变成神经元,并互相联络构成神经网,最原始的神经组织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尔后,这神经网会随着物种机体的复杂化演进而逐步形成周围神经节、低级神经中枢乃至高级神经中枢,但无论如何,它的进化发展都只是为了与有机体的生理结构和生存形式相匹配。
一旦有了神经组织,动物们便会玩儿出许多花招,其中之一就是审时度势、通权达变,譬如我们上面讲述的耗子戏蛇之类。但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这随机应变的本领一定都是运用智慧的结果。实际上,运用智慧倒是经常出错,故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说法。真正的聪明大抵出于“无智无知”的自然造作,就像那处惊不变的老鼠,并非因为它事先通晓蛇的视觉生理才狡猾地选择了佯装静物的举措,而是它那个遇到过度刺激就紧张痉挛的基因编码成全了它的性命。这完全是自然造化和自然选择的聪明,而且是真正至高无上的聪明,须知人的聪明仅限于运用神经和智慧,而自然的聪明却在于缔造神经和智慧。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正是这个缔造一切的自然睿智,始终遵循着两项最基本的法则:一乃“惟求存在”;二乃“通权达变”;前者是变通的根据,后者是求存的手段。所以,在生物进化的闹剧开演之前,先有一场分子进化的序幕出台(从无机化合物到有机化合物、再从有机小分子到生物高分子);而在分子进化的序幕升起之前,又有一阕原子进化的序曲在先(从氢原子逐步遵循衍生出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其他种天然元素);如果再加上粒子进化的宇宙开幕式(从夸克、轻子及玻色子到质子、中子乃至所以亚原子核子等);则真可谓是天条煌煌,一及贯之!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打消一个十分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人”或“活物”才有求存的问题存在。其实非生物亦有,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即自在的方式——求存而已。这个求存的方式就是在面临失存之际变换自身的存在形态,从而也变换了自身的求存方式。换言之,物之变态由于物亦有“不变通即不足以存在”的“苦哀”,人类的通权达变之能无非是秉承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物性之狡黠”罢了。
“唯求存在”——这是通解世事和宇宙演化的唯一钥匙!“变化”是“存在趋于失存”的必须,“存在”是“衰变以求存续”的流程。自古以来,哲人们始终搞不清“在”之永恒与“变”之无常的关系,所以才把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搅成一锅粥。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柏拉图的“形”或“理念”,乃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这一切企图在“永恒”与“流变”之间寻求“存在之本原”的努力,终于全都陷进了混乱的漩涡。以至于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只好从演成“此在”的人性中去敞示“存在”,结果更把“人”本身的问世弄成了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看来,人类的理智是经不起拷问的,因为他们中间最杰出的思想家尚且说不清“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却不在?”(莱布尼茨语),那么,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你还能说清什么是“存在”?什么是“演变”?以及,什么是“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