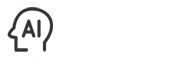王东岳《知鱼之乐》24.天演的自由之路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加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卢梭
人民呵,醒来,挣脱自己的加锁,自由在向你们呼唤!—伏尔泰
唉,一切自由思想家,都没有提防这样的魔术家!他们的自由逃跑了,你指导他们而且诱惑他们回到牢狱里。—尼采
贤哲所追求的不是享乐,而是源于痛苦的自由。—亚里士多德
严复曾经译述过一本《天演论》,其中讲的是人如何与动物一样必须接受“物竞天择”的考验,我在这里也想说一个“天演的道理”,但所要讲的却恰恰是人为什么与动物处在显然不同的“天道位序”上。
人最可珍贵的东西就是自由。但动物决不会有这种主观意志上的自觉和要求,这不是说动物全然不需要自由,而是说它们的社群自由结构必定处于相对满足的状态。据考察,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颇有相似之处,而且越高级的物种,其社群关系越接近于我们人类的原始群落状态。以灵长目动物为例:猴子王国是靠强权来统治的,谁膂力壮大、搏击有方,就由谁担任猴王。猴王的独载和专制照例出于利益关系,作为不太讲究精神格调的猴子来说,他们所关心的主要只有两件事,一是占有雌性资源,二是占有能量资源,前者要靠统霸母猴来实现,后者有赖争抢食物来补给。于是,猴王不仅享有觅食优先的特权,而且整个猴群里的雌性也全都成了猴王的妻妾,其他公猴只能依靠背地里的偷情通奸来打饥荒。不过,一旦猴王病弱或衰老,它便会面临一场极其残酷的政变,要么死于非命,要么孤守残年,这倒也合乎情理,毕竟那权威本来就是强力的产物,今日丧于豪夺,一如昨日取自霸道,所以我们东方人应该对它一点也不陌生。就这样,猴子社会“争取自由”的范围和方式,大约仅限于上述那种“民主偷情”或“造反有理”之类的举动,好在它们不会说话,要不然可能还得加上“言论自由”这项最起码的条款,否则,恐怕就不免会演出一幕幕“文字狱”的悲剧了。
说起来,可怜的中国人同样连“言论自由”的文明史也未曾见过,他们之会说话,只起到了帮着猴子们续演上述那出悲剧的作用。应该承认,中国人祖祖辈辈早已受尽了不自由的苦难,强者窃国,弱者无言,暴动改朝,特权复生。一句话,他们一直处在近似于猴群的社会位相上。然而,国人争取自由的热望似乎历来就没有西方人强烈。近代以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里,“自由”几乎处于完全缺席的地位,所以,人家开来几条破船,就把我们这个诺大的“中央之国”揍得落花流水,实属势所必然; 近代以后,中国总算生出了几个打着“自由”的幌子奔走呼号的人物,但他们到底懂不懂自由的价值却大可怀疑,因为一旦借助这类美好的名义登上高位,他们扑灭自由的劲头总是远比维护自由的兴趣要大得多。所以,仅凭这一点,就不能说我们渴望振兴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那么,“自由”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它为什么会与我们的生存形势息息相关呢?
所谓“自由”,说到底不过是指某个系列的自然衍生物所具备的“自主能动性”。严格说来,一切物质都具有“能动性”,问题在于其“自主”程度的差异,这个自主性就是“自由”或“自为”的规定性。基本粒子或原子的运动速度惊人,但这种运动与它们自身的内在构成或内在要求无关; 分子的布朗运动是各分子要素或离子之间随机碰撞以达成平衡结构的基本方式,这其间已隐约流露出分子形成过程所要求的特定内在素质及其特定运动形态; 最早出现自主能动性的是原始单细胞生物中的一族,也叫原生动物,譬如草履虫,它们的运动方式只比分子运动稍稍前进了一步,即仍然保持着运动形态的随机性,或曰“低自主性”,但却出现了最简单的定向特征,“例如通过一连串的随机动作 (伴随着一些躲避或接近运动) ,最后到达或避开一个刺激来源。这种最简单的行动称为动趋行为 ( Kinesis)。例如放一个二氧化碳的气泡在水中,水中的草履虫在碰到它或游近它时便躲开,这些草履虫随机地游来游去,游近时就走开,最后都在远离气泡的周围。”(引自《普通生物学》)再往后,便出现了自主定向能力更一强的“趋性”运动方式,趋性行为表现为直接趋向或离开刺激来源,原先那种随机摇摆的现象已基本消失,例如灯蛾扑火、蜚镰躲光等等(趋光性)。发展到较高等的动物,仅仅具备趋性这样的自主能力又不够了,例如,初生的小鼠在尚未睁开眼睛以前,如果把它置于一块倾斜的板上,它就会成一个角度向上爬,这是对地心引力的负趋性(趋地性) ,但是当它睁开眼睛看见外界时,这一简单的趋性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它可能不往上爬,反而往下爬到地面上,这个往下爬的动作标志着自主能动性或“自由”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实际上,生物的自然进化演历始终伴随着自主能动性或“自由”程度的不断升华: 从原始动趋反应 (分子运动到生物运动的过渡形态) ——趋性 (原始“感性”初步发生) ——反射 (神经系统业已形成) ——本能 (此时“知性”开始确立) ——“动机”行为(自主意向渐次萌芽),发展到这一步,“自由”已经从“生物自发能动性”朝着“精神自主能动性”的方向逐步转变了。其间穿插着某种日趋深入的学习进程,这个看似高明的“学习”行为,其实早在极其原始的低等软体动物譬如章鱼那里就已开始展现。它的进化步骤大致如下: 惯化学习 (学会对反复发生的无关刺激不予反应以节约机体能量)——印随学习(记忆能力渐增并对日后行为产生指导作用)——联系学习(被若干相互关联的刺激诱发形成预备反应程序)——试错学习(通过行为效果的体验反复调整自身行为方式)——洞察学习(依据既往经验达成处理当前陌生事态的能力和方法)——推理思维(借助概念和一般原则来应付愈益复杂的具体境遇和问题) ,至此,“理性”崭露出头角 (它标志着“智能”从实物对象的束傅中摆脱出来而进入逻辑变塑的异想天开之境界),“自由”跃然于天道(它标志着“体能”从遗传性状的束傅中摆脱出来而进人工具变塑的人机联构之境界) 。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自主能力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从潜隐到显化的主体意志的勃发过程,它使生物的自主活动范围越来越开阔拓展,也使生物的行为自由度倾向于直线增大,其系统演化轨迹是一目了然的: 从一动不动的静态非生命物质; 渐演成原始生物如菌类、海绵和珊瑚的极低动能; 再进化到水母、鱼类的大范围水域活动、乃至水陆双跨的两栖爬行动物; 其后依次是印生脊椎动物的恐龙、飞鸟; 体智灵动程度愈来愈高的哺乳动物如虎豹犬狼等; 再后就是迁徙足迹遍布全球的灵长目古猿和类人猿; 至于人类继续沿着这个挺进线路终于被推向上天揽月、下海捉鳖的失控局面,实在属于不可避免的自然造化。
现在的问题是,宇宙物演的“自由度” (即“自主能动属性”) 为什么必然趋向于增大? 我想,凡是仔细阅读了本书前文的读者,应该已经无需我再来重复那个基础性的“递弱代偿原理”了吧。为了更精确、更明了的阐释上述问题,我在此只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既然宇宙物演的惟一途径就是弱化递进或分化依存,既然任何物态或物种的主观属性发展都是为了追逐自存的条件,则当某类存在者业已迷失于过度繁多的依赖条件或条件对象之中时,相应程度的自主能动性就会代偿性的发生,借以改变被动地遭遇条件为主动地追寻条件,从而力求提高或恢复迎合自身存在条件的几率。即是说,“能动性”或“自由意志”是在依赖条件量过度膨胀,以及与迎合所需条件的机遇呈反比减缩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展出来的属性代偿。质言之,任一载体的“自由度”必与其存在度成反比,“自由化”趋势是生物衍存及其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定。
换一个形象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这样说: 设若有一磐石(分子物质)居然弱化到这般田地,它的体表必须布满神经末梢和种种感受器,以便敏锐地将任何细小的不利刺激转化为“痛苦”的感觉而逃避之; 必须赋有精致的生理构造和运动机能,以便不失时机地将任何微薄的生存条件转化为“欣快”的欲望一概捕获到手; 甚至必须具备逻辑思维能力和选择判断能力,否则便会在苍茫天地之间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 则这块石头也一定得去追问存在和追寻世界,纵然这种追问不免造成愈问愈疑的无穷困惑,甚至,纵然这种追寻不免造成愈追愈失的无限自由也罢——这块软化或弱化了的石头就是“人”! 须知那硬化的石头之所以能够寂然沉默和安然守静,盖由于其存在或依存的问题早在未问和未寻之前就已相对解决了的缘故。这就是自然进化的“失稳”或“失位”态势,“失稳”导致“疑惑”并催生“精神”,“失位”造就“自由”并演成“意志”,此乃“自由意志”或“意志自由”的天道渊源。
说起“自由意志”,西方人对它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尽管论调各异,甚至离题万里,但由此拓展了科学思想的博大氛围和社会契约的人文精神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现实。中世纪前期,奥古斯丁曾经宣扬上帝的意志决定一切,然而他又无法否认人的意志自由,于是他索性把自由意志指斥为人类罪恶的渊数; 正是从这个“罪恶之源”出发,中世纪后期,布里丹才好为之翻案,他将理性贯彻在追求科学的意志之中,强调意志在选择两种看似等价且相互对立的幸福时,其自由的特质最终显示出具有主导作用的人文意义;后来,有人嘲笑布里丹过分忽视客观制约要素可能对“意志选择”的影响,于是设问: 如果一头驴子面对两垛完全均等的草料,它是否会因无从选择而饿死自己呢? 这就是所谓“布里丹的驴子”( Buridan's ass)的自由选择悖论。且不说这头蠢驴该怎么办,人总归是要争耳自由的,它的道理早在裴多菲的那首著名诗歌中尽显无余,只是还需要我们给以更深入的全新注解,因为,作者本人也许尚未意识到,他那层层递进的诗意简直就是“生物社会化演历”和“生物自由化进程”的生动写照:
生命诚可贵——发生于38亿年前的太古宙时期,“贵”就贵在它是从死物中活化的“启下承上之衍存者”,此刻的生命,其自由能动度极低,社会结构度也极低;
爱情价更高——发生于五亿七千万年前的古生代寒武纪前后,“性分裂”是自然分化的继续和社会结构化的开端,此刻的生物自由度虽然有所扩展,但自由的结果却是必须将自身强迫性地嵌合到性别残化的生机重组结构中去,此乃 “生物社会”从低级亚结构状态进入中级结构化状态的开端;
若为自由故——“生物自由”天演而成,“社会自由”是新生代文明化以后才面临的自为性代偿问题,也就是说,当自然分化进程跨越了体质性状残化阶段而步入更全面的智质性状残化阶段之时,性别组合式的亲缘社会形态即动物社会和人类原始氏族社会已退居次要地位,拚着老命去争自由,其实不过是在为生物中级社会跨入人类晚级社会这个更高层次的自然结构化要求献身而已;
二者皆可抛——之所以会如此奋勇无前以至奋不顾身,乃是由于此刻的“无自由则无以存续”,一如此前的“无性爱则无可繁衍”,即是说,高层位的分化物如高度智慧化的人类,必须达成相应的高层位结构态如高度自由化的社会结构,才能够实现自身及其同类全体的继续衍存。
在这个以“自由”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自然进化阶段上,任何有损于载体能动性发挥的机制,必然同时就是造成该载体自身崩溃的同一机制。犹如一头堕人陷阱的猛虎,无论它有多么强悍的生理机能,只要它无法获得自由则必死无疑,因为它的任一生理机能都必须在自主能动性的基础上才有望得以施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巍巍然雄据一方的某大国,仅仅由于害怕个人电脑和外设打印机之类的东西可能危及它对国民青神的空制,就对其严加限制,当时西方有人预言,它的末日临近了! 果不其然,短短数年之后,这个远比猛虎更要威风的庞然大物轰然解体,以至于令它的敌国都感到有些猝不及防。此一结局显然不是敌人或对立阵营策略上的胜利,而是上苍或自然规律赠予蔑视自由者的天赐报应。这也真应了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谶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国力就是其国民生物能的总和。如果每一位国民都备受压制,难以伸展,即让自己潜在的生物能力得不到释放和发挥,国力焉能强盛? 这是一道最简明的加法算术题,何需其他论证? 所以,当今天下,对内最自由的国度,一定是最有实力也最有资格对外称霸的超及大国,尽管它四面树敌,令人生厌,尽管它的人口未必最多,它积蓄力量的国史也未必很长,甚至,由于自由散漫,它的国民最难约束,它的军队最怕死,可它照样横行无忌。这种情形,全赖于群体化的代偿充分状态。
“自由”诚然是一种载体弱化的代偿产物,但“不自由”直接就是失却代偿的灭归取向。换言之,人类是靠精神代偿维系生存的至弱物种,而“意志自由”是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基础属性和代偿前提: 限制自由就等于泯灭精神,泯灭精神无异于摧残入性: 古罗马有一位皇帝叫马尔库斯·奥勒留,在位时饱经变乱和忧患,此公稍具哲思头脑,属斯多葛派的最后传人,加之身居高位,适足俯瞰人寰,却终于只留下这样一句注解“人性”的名言: “人就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尸体”。倘若泯灭了这一点灵魂,或者,倘若剪断了灵魂赖以腾飞的自由之翼,“人”作为宇宙物演最后也是最高贵的存在形态,岂非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般的臭皮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