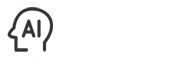王东岳《知鱼之乐》13.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
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罗素
18世纪初叶,爱尔兰籍的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牛顿光学研究和洛克感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怪诞的“非物质假设”,可以用后来变得十分有名的三句话来加以概括:“存在就是被感知”; “物是观念的集合”; “对象和感觉原是一种东西”。在当时,他的思想只被人们视为荒谬的笑谈,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得了疯病,建议他进行精神治疗,这可真是人类史上又一桩傻瓜嘲笑智者的典型案例。要知道,正是贝克莱首次提出了一个逻辑学上的重大悬疑,即感知和理智的终极无效性问题。而且,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启示,休漠才不得不重新探讨经验本身的有效限度,从而揭开了人类深人研究精神本质和认知动量的新篇章。
本来,说到底,人类的认知活动无不建立在“不自觉武断”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你的知识平台下面是一个怎样的空洞或深渊。譬如,我们认识一个物体,无非基于它的形、色、声等感觉要素,但有关“形”的信息主要来自视觉,而视觉仅仅反映该对象的发光或反光属性,倘若某物既不发光也不反光,则对视觉来说它就不存在。所以,古人从来找不见空气,尽管它是地球上最普遍存在、且与人类关系最近的东西,只有等到冬天,人们看见雾状的鼻息,才指之为“气”,可那其实不是空气,只是冷凝成团的水分子罢了。至于“色”与“声”,则更属自欺的产物,前者是光谱波长的主观转换指标,后者是振动频率的听觉转化感受,况且,你又没有任何一种感觉以外的手段,能让你把那声色迷离的物体通过另外的途径摄入意识,以作参照。若然,你凭什么确认你的感觉对象一定客观如实,而不是某种不自觉的主观武断呢?
也许,你会说,我的理性和思维可以助我做出正确的判断。错了! 敢问古人难道就没有理性? 或者,爱因斯坦以前的物理学家都不会思维? 否则,祖辈先贤们何以不能指认气体的质量? 身为科学家又何以会误判原本可能并不存在的“以太”遍布宇宙呢? 实际上,理性思维的武断性大概还要更严重一些,因为,理性活动无非只有如下三种方式,而这三种用智方式偏偏又没有任何一种是足可信赖的。
先来看第一种方式,也就是纯逻辑的推理和思辨方式,想必这种方式最能避免感性的干扰吧。古希腊有一位数学家兼哲学家,名叫毕达哥拉斯,他最早意识到感觉的混乱性,因而提出“世界是数”的唯理论主张。“数”当然具有最完美的逻辑秩序和规则,也能最透彻的整顿感性表象的凌乱无序和浮浅。然而,问题是,怎样才能证明世界就是数,或数本身的逻辑运算规则一定就是世界的运动规则呢? 这个问题恰好就是贝克莱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让我们换一个讨论方式,譬如问: 逻辑运动究竟是按照自身固有的程式自行展开呢? 还是通过某种可靠的感知通道真实地反映着外部世界的运动程式呢? 这一问,你将立刻陷入哲学上那个永劫不复的泥淖——举凡你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东西,正是你应该加以证明的东西,或者说,所有你能拿出来的证据本身,恰好就是你要证明的对象,这使得一切证明都落于无效,也使得一切证伪都落于无效。除非你盲目地事先假定,你所给出的任何东西或证据都是精神源性的,或者都是外物源性的,那么你的所有证据都会立刻有效,而且足以充分自如地互相印证。但是,这样一来,你原本所拟探索的那个最基本的“知与在”的本质及其关系问题就仍然只是一个武断。可见哲学史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在逻辑上纯属无意义,难怪维特根斯坦认为,既往的此类哲学争辩统统都是语言病的产物。
第二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归纳法,这是人类用智最常见的方法,也是借助于感觉和经验来积累知识的最直接的渠道,看起来,它似乎兼有感性与理性的双重优点 (我们暂时不管感官造成的先决性误导,只去关注理智本身的运作特点) 。不过,问题在于,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归纳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伪不能证明的偏见,然后,你还必须用这种以偏概全之知作为验证所知的根据,因此到头来依旧不过是一局彻头彻尾的武断罢了。譬如说,经详细调查,你发现亚洲的天鹅是白色的,欧洲的天鹅也是白色的,美洲的天鹅还是白色的,于是据此得出凡天鹅皆为白色的结论。可你毕竟未能一一考察世间所有的天鹅而使之穷尽,因此作为一项证明它是无效的。虽然如此,你还是得将上述结论作为有效证明姑且武断地接受下来,否则,你可能陷于永无所知的困境。如果有一天,澳洲的黑天鹅作为有效的证伪项亦被归纳进来,你的所知不免顷刻间崩溃,而且,为了谨慎起见,你最好不要再对天鹅的颜色作什么结论,尽管诸事皆处于这种无知状态又为你的生存所不允许。可见,归纳法是如此糟糕的武断求知之法: 它要么导致误知,要么导致无知。然而你却不能因此就说,以前的误知还不如今天的无知,因为你终究得靠武断的误知,才使自己显得略有所知。
第三种方式乃是同样常用的演绎法,它是借助于理性来进行判断和推论的最主要的逻辑通道,并且它还有一个极具价值的特点,那就是可以从已知之中推出未知,因而似乎有望成为人类知识增长的基本生发点之一。然而,情形与归纳法刚好反了过来,即,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演绎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明不能证伪的偏见,而且,由于你借以进行推演的根据恰恰来自于有限的归纳,因此看起来似乎成立的证明其实不过是建立在武断基础上的武断而已。譬如,从大前提出发,说: 凡属天鹅者皆为白色; 小前提是: 澳大利亚也有天鹅; 则借以得出的结论便只能是: 澳大利亚的天鹅必定同样是白色的。单从逻辑学出发,此项三段论式的推理证明成立。然而,对于这项证明的可靠性,你却根本无从求证,即完全没有逻辑上的证伪之余地。因为如果你去实地考察,发现澳洲的天鹅竟有黑种,则作为证伪这已是归纳法的证伪,而不是演绎法的证伪了。除非你借以进行演绎的根据全不与归纳相关,而是来自于所谓纯粹逻辑的公设和推导 (假如神学、形而上学、几何学或数学演绎算是如此的话) ,那么,你又不免顿时陷人前述第一种方式的那个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循环论证之中。
如此看来,不自觉的武断同样是理性之知的前提。
那么,武断之知可否被叫做“知”? 或者问得更贴切一些,即武断之知如何成其为“知”?
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于反证的方法来求解,即通过抽掉那个潜在的武断基础,看看“认识”的格局还能否达成。
哲学上一般是这样划分的: 指谓具体之对象或存在物的学问乃为一般的学问或科学的学问,而对“指谓”本身加以指谓的学问就是哲学或形而上学。前者是在“形而上之中”求知,后者是对“形而上本身”研修; 前者表达为指谓存在的存在者与指谓对象的依存关系,后者表达为指谓存在的存在者对自身状态的自我意识。
然而,这里马上发生了一个悖论——
作为前者,他虽然自以为知道自己所关注的“对象”为何物,但由于他全然不知自己借以关注对象的那个“关注”本身为何物,即不知自身之“能指”如何作用于“所指”,因而其“所指”究竟为何物到底仍旧是一个疑团。所以,纵然是身为科学泰斗的爱因斯坦亦不太那么自信,他曾经说:“一切科学,不论自然科学还是心理学,其目的都在于使我们的经验互相协调并将它们纳入逻辑体系。”(引自《相对论的意义》)显然,此处已先有一个必须对“经验”和“逻辑体系”之类的东西加以澄清的问题存在。
作为后者,他其实根本找不见那个形而上的“能指”本身,一如眼睛看不见眼球自己一样,他所谓的“能指”必是已经包含着某种“所指”的“能指”,就像一旦说到“视力” (“能视”) 必得借助于某个“所视”才可以将“能视”抽象出来一样。既往那些具体化了的“能指” (如理性、逻辑、精神等等)因此皆已成为“所指”,犹如眼睛一旦看到了“眼球”,那眼球对于“能视者”来说已是摆在解剖台上的“所视”而不是“能视”了。所以,从柏拉图到贝克莱,举凡企图以究察“能指”来澄清“所指”者,非但未能说明“能指何以能指”,反而终于连“所指”与‘能指”何者真存都一概迷失了。为此,维特根斯坦不无道理地指出,“命题能表述整个实在,但它们不能表述它们为了能表述实在而必须和实在共有的东西——即逻辑形式”,因此属于“不可说,而是显示其自己”的东西,而“真命题之总和即是全部自然科学”(引自《逻辑哲学论》)。
结果,兜了一圈,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原先那个一无所知的起点。
反之,假若爱因斯坦或维特根斯坦不去对那个“潜在的武断”加以质疑,则知者非但无疑于其“知”,通常倒是自以为这个一时所得的“武断之知”就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显现”。
于是,可以肯定地说: 恰恰是武断才成全了“知”。
“武断”一词,就其原义而言,是“以无知为知”的称谓——也就是说: 如果从一般概念上推论,则“知”不成立。但无可否认的是,人们历来觉得自己确有所“知”,而且,惟因有“知”,才得以生存。
那么,我们必须重新发问: 什么叫做“知”呢?
这可是难倒了所有哲人的一个千古悬案,严格说来,此前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此问题真正给出系统的论证和解答。自柏拉图以降,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想揭一开这个谜底,并且常常自以为完成了这个使命,只有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一开始就自谦地宣称: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旨在提醒人们应当特别小心“对知的无知”。然而,如果我们连“知”是什么都糊里糊涂、昏然不识,那么,不妨检讨一下,我们大家究竟还应该抱有多少侈谈“真理”的雄心和雅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