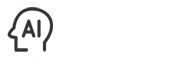王东岳《物演通论》之跋
本书无非是把一回事演绎成了三件事,或者说,是把一个系列的事体人为地分立为三个系统加以诠释,即:事物或世事之所以流变不息,以至于演化出人的存在、人的精神和人的社会,全是由于一个最简单的原因使然——我称其为“递弱代偿原理”。
因此,不管对上述原理加以论证显得何其困难,读者其实只要能够得出如下三点结论即可欣然掩卷:
其一,自然物演呈现为在流逝中常存、在衰亡中新生,由以嬗变出从简到繁、属性渐丰、结构重叠的宇宙万物和人间气象,盖由于物质存在度不可逆转地趋于递减,从而要求相应形式的代偿过程予以追补所致;
其二,精神现象说到底不过是原始物理感应属性的代偿性发展产物而已,由此渊源出发,才能揭示精神发生和精神运动的全部规定性,并借以廓清久久笼罩在认识论、意志论以及美学理论上的种种哲学谬误;
其三,社会存在是衍生于生物存在之上的又一层代偿物相或代偿存态,亦即生物分化及其生物属性分化正是社会结构分化的自然基础,因此以生物为其基质的社会实体自有与生物进化史同步发展的自然演运史。
将如此简明的事理搞成如此复杂的书卷,实在是因为整个人类思想史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歧见纷呈,云遮雾障,以至于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小心地拨开草莽和荆棘,才有望在可供落脚的地面上踏实一条路径。
哲学大概总归要处于两难境地的吧。在思想史早期,哲学倾向于凭借感性直观表象来否证感性;而今,哲学又倾向于凭借理性科学逻辑来质询理性;这使得哲学不免陷于如此尴尬的局面:它先行捣毁了自身赖以立足的基础,然后却又说它似乎才是唯一站得住脚的学问。然而,回首远望,当代科学的最前沿,譬如粒子物理学,不就是两千多年前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所提出的“原子论”哲理的继续吗?也就是说,科学观念作为哲学思脉的传承产物,其本身不也照例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再说,假如由理性所导出的人类现实生存境遇未曾给我们造成麻烦,或者,假如由科学所导出的人类逻辑延展序列未曾给我们提出疑义,哲学又怎么可能去凭空诉说呢?因此,一味地鄙薄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反倒是当前的科学进程及其理论形态愈来愈呈现出某种超脱具象的思辨化趋势,很值得思想界予以关注。它可能恰好预示着,人类既成的认知拓展方向,正无可避免地奔赴于越来越空泛亦即越来越茫然的高危境界。
也许,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种种哲学问题,将来同样会转化为一系列科学问题或后科学问题亦未可知(我更倾向于认定它是科学时代促成的小问题,却是后科学时代才明确面临且需严肃应对的大问题)。正如罗素所说,凡是尚不能得出确定性和精确性答案的学问即属于哲学探索范畴,“因此,哲学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是真实的,而且还是明显的:有了确定答案的问题,都已经放到各种科学里面去了;而现在还提不出确定答案的问题,便仍构成为叫作哲学的这门学问的残存部分”。(引自《哲学问题》,[英]罗素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就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尽管我也给出了一系看似数学模型的东西,但它实际上分外粗略,以至于目前完全无法代入参数,所以即便它乍一看有些貌似科学,其实照例只能算作一点儿也不时髦的“哲学的残存”或“衰败的哲学”而已。但,哲学的衰微未必不代表“人文的衰微”或“人寰的败落”,故而请你最好不要怀疑它的真实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迫切性。
总之,本书只是提出和论证了一个基本原理。运用这个原理,应该还可以澄清许多我未曾涉及的其他问题,即是说,这个原理具有相当广阔的普解性。不过,那已是后人的事业了,我的厌倦之情早就把自己的灵性埋葬于江郎才尽的荒塚之中,所以只好就此搁笔了。
王东岳
2002年5月30日于陕西师大寓所
(2013年4月及2014年6月稍事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