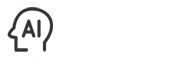王东岳:四、《物演通论》提要——精神哲学论
卷二 精神哲学论:提出和论证了“感应属性增益原理”
(八)依据递弱代偿原理,证明人类的“精神现象”和“感知能力”归根结底就是“自然物质感应属性代偿增益”的产物,这是有关“精神存在”和“认识论”问题的总纲。
(第一次明确指出了“精神”的自然源头,回答了自笛卡儿以来始终存在的“物质实体”与“心灵实体”的关系问题,即彻底清理了“知”与“在”的终极关系问题,将“认识论”问题从“横向二元并立关系”转变为“纵向一元衍存关系”,也就是将既往哲学所争论不休的“认识什么和如何认识”的纯主观问题,归结或还原为“认识的本性在于如何维系其载体存在”的存在论问题。参阅《物演通论》第六十一章至第六十四章、第六十九章和第七十章等。)
(九)通过分析感知方式,证明无论是“感性”或“理性”的运用都不能获得“对象的本真”,从而确认“形而上学的禁闭”或“认知的武断性”,即通过逻辑证明来再度确认“认识的本质不在于求真而在于求存”这一认识论的核心问题。
(这样就消解了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反复争论的“独断论”问题,也消解了哲学史上有关“唯物”与“唯心”这个伪问题,同时还消解了“不可知论”的问题基础。参阅《物演通论》第六十五章至第六十九章等。)
(十)提出“存在效价”(即“存在度”)与“感应函量”(即“感应度”)的反比代偿关系,由以确定“知的上限与下限规定”,也就是要从根本上阐明“存在决定意识”的自然机制和贯彻方式。(于是彻底纠正和深化了马克思提出的这一重要哲学论断。参阅《物演通论》第七十章。)
(十一)提出“感应属性耦合原理”,证明认识过程就是主体的“感应属性”与客体的“可感属性”的对应性耦合过程,从而揭示“对象”与“客体”的差别以及“对象”与“依存条件”的关系;此外,还诠释了认识方式的“最小作用原理”在于以最小代价获得“有效识辩”,从而进一步证明“感知失真”恰恰是对主体衍存的维护。
(这样就彻底消解了“感知求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同时还解答了休谟与康德所悬置的“感知失真与感知效用的关系”问题;另外也回答了“奥卡姆剃刀”即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的实质。参阅《物演通论》第七十一章至第八十一章等。)
(十二)提出“失稳”和“失位”概念,以说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一项不良指标;提出“伪在”和“危在”概念,以说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为何反而不利于人类的总体生存。(一反人们历来对知识能力提高的赞扬态度;系统证明了自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以来西方哲学和科学关于“追求真理”、“追求知识”和“追求进步”的认识论之失误。参阅《物演通论》第二十一章、第八十二章、第二十七章与第二十八章等。)
(十三)提出“位相”和“盲存”概念,以说明人类与一般存在物的共通关系;将“主体”还原到“客体”系列之中,澄清主体与客体的“原始可换位状态”与“后衍不可换位状态”,并提出“感应效能的非对称性”与“依存向度”的关系新说。(参阅《物演通论》第八十三章至第八十七章,解决哲学史上始终将主体与客体分裂的问题。)
(十四)提出对“现象与本质”的新答案,证明“本质”不过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由于演化速率差异导致“位相错动”或“感应关系错落”的产物,由此造成的信息增量和逻辑模型重塑就是所谓的“本质”。(参阅《物演通论》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和第八十八章,解答了哲学史上争论了数千年的“本质”空洞问题。)
(十五)提出“属性耦合”必然导致“抽象先于具象”的结论,也就是说,“简单抽象要素的进行性分化组合”才是“复杂的具象化表象”得以形成的原因。(参阅《物演通论》第八十九章,解决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共相”与“殊象”总被混淆或倒置的问题。)
(十六)提出“感性”、“知性”与“理性”的发生阶段及其域界覆盖关系,证明它们的递进层次就是主体失位和感知失稳的精神演运特征。(一反哲学史上历来将“感性”、“知性”与“理性”仅仅划归于人类的狭隘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它们的自然发生阶段;重新界定了“知性”判断的概念边界;并首次对它们的演进层级和各自状态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负面评价。参阅《物演通论》第八十九章至第九十三章。)
(十七)提出“广义逻辑”概念,揭示“广义逻辑融洽”与“广义逻辑失洽”的动态内涵,把逻辑史和逻辑进位与自然物演进程贯通,证明“狭义逻辑”之前的低端感知方式也存在着潜意识或潜结构的生理整顿程序,这样才能阐明逻辑的渊源和逻辑序列的代偿效能。
(非此不足以澄清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合理性,也不足以梳理形而上学禁闭的系统性,更不足以阐明感知代偿增益的总趋势。而且,这个“知识论”模型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生物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持。参阅《物演通论》第六十五章和第六十六章、第九十四章和第九十五章,以及第一百章和第一百一十八章等。)
(十八)在“狭义逻辑”范畴内,提出“形式逻辑”的原始起点在动物“知性”阶段;提出“辩证逻辑”是理性逻辑的初始阶段;提出理性逻辑的高级阶段是“理想逻辑”;提出“理想逻辑”四定律;并就“理想逻辑”的性质、状态及其失对应性可能对其载体或主体带来的负面作用提出证明。
(这些都是全新的观点,是从哲学存在论的高度首次对理性逻辑的高级阶段给出总结性论证;附带也可以佐证康德对理性的持疑和波普尔对科学的界定。参阅《物演通论》第九十六章至第一百零三章。)
(十九)从超经验性“试错法”的高度,在“感知无不失真”的认识论前提下,提出了有关检验任一逻辑模型或理论体系是否“正确”的标准,即“逻辑三洽定理”。(这是康德以后的所谓“唯心认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它是从另一个更具体的侧面继续回应“感知失真与感知效用的关系”问题。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章。)
(二十)提出“意志”在感应属性或精神系统中的确切定位,建立“意志”与“感知”的对应构成关系;诠释“情绪”性心理感受和心理波动的客观动势与主观效应;阐明“逻辑”与“意志”的统一感应代偿作用。(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意志论”哲学的空白;同时有助于叔本华哲学的精义与失误。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二十章。)
(二十一)提出对“美的本质”的全新阐释,说明“自然美”与“艺术美”各自得以发生的特质,证明“美”与“审美”对载体生存或主客体依存的维护效应,首次把美学问题奠定在哲学存在论的基础上。(从终极意义上的“存在”基底部出发,解开了柏拉图关于“美是难的”这样一道千古难题。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一十二章至第一百一十五章。)
2007年8月21日凌晨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