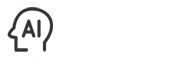王东岳《知鱼之乐》19.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圈套
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赫拉克利特
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赫拉克利特
“真理是弯曲的,一切直者皆虚伪,时间之自身便是一个环。”侏儒鄙视地咕侬着。—尼采
大成若缺,其川不弊。大盈若冲,其用无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呐。—老子
一种思路,如果老是从原点出发,兜一个大圈子后又返回原点,那就是典型的循环论证。好比有人问:“人是什么?”答曰:“人是理性动物”。可如果你还想深究一层,再问:“理性动物是什么?”答案却又转了回来: “理性动物是人。”结果,你从谓语中的所得终于丝毫不比主语中的所问多出什么,这就是辩证法。据黑格尔自己说,他的哲学就是这种“像圆圈一样”从“绝对理念”出发、最终又“回复到自身”的逻辑系统。但你应当小心,这类圆圈通常恰好就是一个圈套。不待说,这个圈套首先就套住了黑格尔本人。
说起黑格尔,中国现时稍懂一点儿哲学的人,无不对其存有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大家开口“辩证法”,闭口“矛盾论”,闪烁其辞,跳跃两端,真有玩儿不尽的滑溜和机智。不过,我却有些怀疑,到底有几个人真正弄通了他的思想? 一般来说,对于一种学说,如果你不能有所超越,那么你就不太可能完全读懂它,尽管昂首批判它的人——譬如费尔巴哈——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糊涂蛋。
让我们先来看看,黑格尔哲学究竟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起初是率然追问身外的世界,即“存在的本体”,如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时期; 尽管随之也发现了所欲追问的世界总不免折射出追问者自身的精神痕迹,或“理念的背景”,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尤其是柏拉图; 但终究未曾想到或未曾证明,对自然本体的设问本身 (即“本体论”) 直接就关联着对精神本体的设问。
直至公元17世纪,笛卡尔敏锐地意识到,所谓“外部世界的存在”总须被统摄在精神之中才成为可以指谓的在“存在”,从而提出,只有“我思”是惟一可以证明的存在,由此开创了近代“认识论”的先河。不过,从直觉上,笛卡尔又不能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于是,著名的“二元论”就此诞生了。
然而,一系列问题也由此发生: 既然“心灵实体”是惟一可以确证的存在,那么,怎么能够又说“物质实体”存在或不存在呢? 这岂不是明摆着要为自己认定不能证明的东西予以证明吗?显然,笛卡尔从“怀疑”出发却走入“独断”。合理的推论应该是: 精神以外的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一概不可知。这便顺理成章地造就了休漠。
既然“不可知”,何以又会“有所知”? 知性——哪怕是“纯粹知性”——这时总该探讨一下了吧,否则,说什么“可知”或“不可知”不是照例也属于一种“新的独断”吗? 康德就为此思索到老,并成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着意拷问“知的规定性”的近代第一人。诚然,他的这番努力不可谓业绩不著,但终于还是未能澄清“知的规定性”如何与“在的规定性”统一,反倒更弄出一大堆“二律背反”的麻烦。
至此,必须有人出来收拾这个残局:他既不能又跑到“精神”以外去独断地大发议论,亦不能全然置精神认知的“对象”于不顾,同时,他还得设法消解康德及其前人所提出的知性或理性中的种种矛盾和混乱。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即便他运用某种穿凿附会的方法,只要能够一举解决如此复杂的一揽子问题就值得给以大大的喝彩。于是,黑格尔那“辩证的绝对的理念”之光辉一时把人照得眼花缭乱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后,便有人说,黑格尔是哲学的终结,此言不错。因为黑格尔确实将传统经典哲学表面上的所有漏洞都填补起来了,相应地,他同时也就将既往哲学的深层不足暴露无遗: 那就是,他不能说明“精神本身为什么会存在” (所以他就只好乞灵于一个独断的“绝对精神”),以及,相应的,他也不能真正说明“精神本身如何存在” (所以他就只好乞灵于那个老朽的“辩证方法”)。
显而易见,黑格尔的目的只是想要澄清,“封闭的精神系统”如何才能与“整个存在系统”相统一。也就是说,辩证法不过是他临机借来的一种逻辑狡辩工具而已。
那么,对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本身,我们究竟应该给它一个怎样的评价呢?
简言之,古猿刚一变成人,辩证逻辑就开始捉弄这帮可怜的新生命了。也就是说,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理性逻辑的成熟表达,而是理性逻辑的幼稚体现,黑氏的功劳就在于他居然能够将如此稚嫩的逻辑思绪给出如此淋漓尽致的逻辑阐发。一言以蔽之,辩证法是理性逻辑最原始、最低级的过渡形态。
有史为证: 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以前,辩证法就已经通行于世了,所以,中国人历来把老子的辩证思想称为“黄老之学”,即从东方的第一个文明先祖“黄帝”开始,所使用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辩证逻辑。再看,中国最早的一部经书《易》,里面充斥着阴阳辩证的所有花样,那是后人对原始部落惯用的占卜术所作的文字化整理,其中的基本符号“爻”,实际上就是原始人用折断的树枝或吃剩的残骨,摆出来代替文字的占卜图形。西方也不例外,早在古希腊,大多数哲人或智者都是辩证思想家,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以及苏格拉底等等,只不过,严肃的希腊人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诡辩术”,因此,真正的学者从来不屑于将它视为研究的宗旨,顶多偶或借来穿凿一下当时实在说不清楚的难题。所以,亚里士多德精心研究逻辑学,却反而给出了被我们称为“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形式逻辑三大定律,即“同一律”、“排中律”和“不矛盾律”。也就是说,亚氏认为,在逻辑上出现矛盾是不允许的,是思维混乱的表现。这一点,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及其科学理论也同样严格地予以遵循,尽管他们是在更高一级的理性逻辑层面上遵循之。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产生一丝反感,以为我完全是在刻意贬低辩证逻辑,其实不然,我只不过是要把辩证法摆在它应有的位置上,而不肯让它虚发高热罢了。惟因如此,我倒认为,黑格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说成是“知性逻辑”,实属一言中的,只可惜他犯了两项根本性的失误,结果导致罗素给了他一个更低的评价:“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是错误的”。这两项失误是: 第一,他未能说明人类理性及其精神现象的自然渊源,于是他当然也就说不清知性逻辑的真正内涵,即他不懂“知性逻辑”是典型的“动物逻辑”,而人类的“理性逻辑”是从动物的知性逻辑中增长出来的; 第二,他因此同样未能说清辩证逻辑在自然逻辑演化史上的自身窘况和发展前途,即他虽然承认辩证理性只是达成思辨理性的中间过渡阶段,但他终究无法阐明思辨逻辑的运动规律,亦即无法摆脱沿用三一式辩证合题的方式来图解理想逻辑的陈旧套路。
我在这里不想把话说得太深,只想谈一些有趣的话题,滤掉一些过于明显的缪见。现在先谈精神现象的由来: 所谓“精神”,过去都认为它是人类独具的理性状态或理性气质。但这样看问题,你永远也说不清“精神”的本质和规定,既往的哲学——包括黑格尔的思路——之所以颠三倒四,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实际上,按照“万物一系”的自然演化原理,“精神现象”无非是原始物理“感应属性”的代偿增益产物罢了。也就是说,随着自然物演存在度的不断递减,后衍物质的分化依存属性相应递增,它经历了从原始理化的“感应”。低等生物的“感性”、后生动物的“知性”、晚近人类的“理性”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从“感应”到“感知”的进化过程。问题在于,越进化、越高级的物种,它的存在稳定性越差,表现在它的“主观属性”上,就是它的感知状态也越来越动摇。譬如,粒子之间的电磁感应是极准确极稳定的,它们各自的依存对象只是单一的对偶关系(“感”与“应”瞬间同时完成,即“感应一体”) ; 原始生物的感性相对而言也还算牢靠,那时的主体感性器官很简单,即尽可以不对太多的外物产生感觉(“感”与“应”相继发生,即“感应迟滞”); 但到了脊椎动物的知性,情形就有些麻烦,因为它必须面对高度分化的诸多依存对象,这就出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形式逻辑”或“知胜逻辑”。所谓“知性逻辑”,其实就是所有后生动物(譬如脊椎动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的本能识辨反应或直觉判断能力,这个判断反应程式是被各物种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因而它当然是静止不变的。之所以说它是“知性”,乃由于它必须在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感性表象上进行诸多对象的选择判断,好比一只麻雀,它既能看见树枝和树叶,也能看见种籽和毛虫,它会本能地在这幅表象上做出选择,判断如何绕开树干,直扑可食的种子和毛虫,这里表达着最原始的“同一律”,即决不发生识辨上的混淆; 及至进化到哺乳动物,譬如一头非洲狮子,它光有“同一律”已经不够了,因为它所面临的对象更多、更复杂,比方说,它要在较多的猎物中进行选择,并要在各猎物的不同分布状态下考虑怎样才能较有把握地获得成功,于是,“排中律”和“不矛盾律”应运而生,作为它防止判断动摇的辅助法则。实际上,人类日常活动中的反应,大多还是在使用从动物那里继承过来的知性,或知性与理性的混合。可见,知性有两条特点或优点:第一,它在对感性表象进行本能的或直觉的选择判断之后,当即就可以发生具有针对性的反应行动(“感”与“应”尚未完全分裂); 第二,因此,相对于理性而言,它是一种较简捷、较稳定的高效识辨系统。其缺点是,如果你不得不面临更趋复杂化的对象依存关系,它就会显得难以应付了。
理性由此应运而生。它的特点是,在知性判断完成之后,主体还是拿不定主意,亦即处在判断动摇的危机状态,于是,他只好将知性判断的结果转化为“概念”,以便在行动前对该项结果继续推敲,或在一系列更繁复的概念之间进行推理,这就是理性(“感”与“应”完全分裂)。既然把知性后面的“行为”变成“概念”是由于对知性判断发生了动摇,那就必须进一步琢磨那闪烁不定、左右摇摆的“概念”本身,或者说,必须进一步测度那内涵不确、外延不清的“概念”边界,这就是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得以产生的初衷。所以,无论是东方的孔子,还是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告诫人们,请你在行动之前,先去探求两端,以便最终找到不至于让你碰壁的“中庸”出发点。例如,柏拉图说,“勇敢”是介于怯懦(“软弱”)和鲁莽 (“激情”) 之间的恰当分寸 (并且必须在“智慧”的掌控之下,由以还能显示出个人人格上的“正义”质素云云),这话说得很漂亮,可当你真正面临手持凶器的歹徒抢劫时,你到底该在偏于怯懦或偏于鲁莽的哪一个具体点上表现勇敢,却实在是一桩格外费思量的难题,迫于形势,恐怕你只好再把自身行为的控制权交给知性,即立刻凭借性格天赋和本能判断,决定逃跑、告饶、谈判还是搏斗,至于最终结果是什么,那就不好说了,但总比你呆在那里进行一番没有任何确切量度的辩证思考要强一些。
人类就这样掉进了辩证逻辑的圈套,因为你必将碰到越来越多的比遭遇强盗更复杂的间题。然而,上述例证表明,辩证逻辑只能让你游移不定、首鼠两端,它虽然是与你生存状态和感知状态相适配的必然产物,但也仅仅是一个分外困窘的理性初始过渡阶段,你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上洋洋自得,而是要么在简单问题上退回到知性逻辑那里,要么就必须向前推进到理想逻辑的境地。所谓“理想逻辑”,是指在极其复杂的对象两端或多端对象之间进行细致入微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就像伽利略用归谬法的“逻辑实验”来证伪亚里士多德的落体原理,或像爱因斯坦用虚拟法的“理想实验”来建立相对论那样。说得简单一些,譬如黑格尔曾讲: “生命的每一瞬间,是生,同时也是死亡。”但这样讨论问题,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现代科学逻辑证明,在多细胞生物中,生命尽管在每一瞬间都有体内细胞的死亡和更新,但每一种细胞的增殖代数是有限的,即随着细胞增殖过程的发展,细胞染色体上的端粒体倾向于渐次缩短,直至停止分裂、生命死亡为止,这是一个单向度的进程,决没有双向跳动的可能; 再看生命的起源,它是从分子进化中演变而来的,而且随着生物进化的继续前衍,越晚近、越高级的物种,其生存力度越衰竭,直至生命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为止,这也是一个单向度的进程,也同样没有辩证轮回的任何可能性; 这才是生命运动的本质、渊源和趋势。放眼整个宇宙,能量运动的“熵”照例倾向于不断增大,这个一点儿也不给辩证法留面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预示着辩证法在诺大的自然界里根本找不见它的立足点。
我无意否认辩证逻辑的存在,它是整个自然感应发展和生物逻辑进化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我一点儿也不想崇拜它,因为它实在只是人类理性逻辑的最低水准。限于篇幅,也限于此书的读者群体,我不想在这里接着讨沦理性逻辑的纵深状态,那是一个过于枯燥的专业话题,你不去钻研它,大约也不太妨碍你的思维逻辑跃迁到较高的层级上。然而,如果你痴心坚守着那个辩证法宝不放,那你就只好去体验一下固步自封的滋味了,仿佛一个落伍的人掉队太远,早已看不见前面的人群,却还以为自己在独步天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