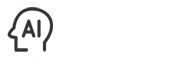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物演通论》:第一百一十五章 艺术之美
既然“美”是介于感应分离之间的一种精神代偿方式,则在“美”里面必定暗含着某种服务于远隔的“应”的基本要素,自然美是如此,艺术美亦不例外。否则,纯粹漂浮在“感”(未必仅指“感官之感”,而是扩展为感性、知性、理性之总和或其中任一部分的那个“感”)上的“美”非但不免流落为无所谓“美”的无聊,而且连“感”也将还原为无所谓“感”的麻木。
也就是说,“美”必须有“应”的遥相返照,才能在“感”的底版上曝光显影。
于是,随着“感”越来越漂离于本真或元在,“应”及其“意志序列”也就越来越显得无以为应或应于缥缈,以至于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尼采语)——所谓“追求”就是“应”或“意志的奔突”,所谓“追求虚无”就是“应的无着”或“应的渺茫”,此乃从自然美之中逐步衍生出艺术美的天演源脉。
【黑格尔的美学只承认艺术美,亦即只承认理性层面的美(用他的话说叫作“理念的感性显现”),足见他的美学观并不比柏拉图进步多少,尽管他就美学问题发表的议论特别冗繁也无济于事。】
换言之,艺术美不是简单的“非应”或“无应”,而恰恰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更广大更深刻的“应”的代偿,即随着“感”扩容为面向无垠存在的无涯理性,“应”一方面在理想层面(即理性层面)上聚焦为执着的“志向”,另一方面在心理层面(即知性层面)上沉淀为强烈的“美感”,由以暗导和辅助漫化开来的“应”。
可见,艺术美仍然是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或者说,仍然是一种应的蓄势待发状态。从这一点上看,艺术美与自然美同质。
【所以,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艺术欣赏倾向,这是由于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意志倾向或“应的向往”使然。虽然如此,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悲剧艺术历来被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最深刻最普遍地反映出(并关怀着)“艺术美的载体”(即“艺术受用者”)的“应”之最终也是最无奈的结局和宿命。】
因此,“美”像其他精神现象一样,必有一个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漫长的演化过程。而且愈原始的“美”一定愈深沉而常存(如千姿百态的自然美),愈后衍的“美”一定愈浓烈而短寿(如各种形式的艺术美)。
【诚然,“美”的产物总比“理”的产物要耐久得多,那是因为“美”毕竟是回落到意向性心理(或知性)层面上的东西;它之所以更震撼人心,乃是因为人类目前尚处于以知性为其精神主体的阶段,理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冰山之尖而已。故,“美”与“理”呈现出这样的表面矛盾态势:从前体代偿的深度来讲,“美”强于“理”;从后衍代偿的烈度来讲,“理”强于“美”;因此倘若骤然让你比较“美”与“理”何者更雄奇伟岸,你不免哑然。】
关于“美”的问题,我只能如此简而言之,因为“美的本质”或“美的哲学”就是如此之简,多言无益。
【至于有关“美”的具体应用及其细枝末节的学问,自应留待各个分科之学(如美学、心理学或神经生理学等)去分进合围,才有望周全。哲学最好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才不至于令自身变得空洞无物,大而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