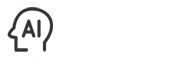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物演通论》:第一百一十四章 美的渊源
根据上述,似乎可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美的渊源,并初步窥见了美的质素,那就是与感应属性同在且与意志的源流并驾齐驱的“未应的感”或“虚拟的应”。换言之,如果说“意志”是“应”的精神化变种,则“审美”就是意志的“非应式”变种。
【具体地说,“应”是依存的实现,是有所依赖和有所进取的“意志”的操作,由此形成意志的中轴;反之,“非应”是未实现或不现实的依存,它处于有待依赖和有待进取(是乃“应前的魅惑美”),以及无所依赖和无所进取(是乃“应后的观审美”)的意志的周边;故可以将“美”形象地视为应的精神光环或意志的虚幻光晕。】
显然,“美”的前提是感应分离,因为“感”与“应”的一触式兑现必令“美”根本没有发生的余地,而且,正是由于感应分裂才造成了难以兑现的应之焦灼。换言之,美的余地在于“失位”——即在于感不能当即达于应以及应不能当即终结感的那个感应失离的空隙之间,或者说,在于感之不真以及应之不切的那个感应裂变的错位之间。
【所谓“感应分离”,就是对未“应”之“感”的牵挂或向往,因而“未应”所表达的就是“与关注对象的依存失离”,无论这“失离”是“暂无利害牵挂的应前观照”抑或是“无从利害牵挂的应后观审”。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是无关利害的、不带任何意图的或无欲望的鉴赏判断之愉悦,就是对此种情形的表观描述。康德还把审美诠释成以感知和想象为方法来审视或审判万物的人本认知过程,借以排除神本宗教系统的无谓干扰,但他却没能将一般感知与特定审美的内在关系和根本区别澄清开来。】
不过,如果进一步追查,我们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正源于“感”的本性,即源于作为“应”的前提的“感”一开始就是属性耦合的那种感的失真性:基于此,才会发生感性阶段的“有声有色”的变态模拟;才会发生知性阶段的“声色迷离”的辨析表象;也才会发生理性阶段的“滤清现象”的有序反思;从而完成了自“水彩着色”到“结构布局”再到“回眸观审”的美化全序列。
也就是说,“感”的失真以及在精神代偿的进程中之愈来愈失真,才是造成感应分离的更深在的原因——正是由于“感”的失真及其愈来愈失真,方才造成随后的那种感应裂隙,以及为弥合这裂隙所代偿派生的应前魅惑和应后观审。可见,所谓“失位”,失就失在感的愈来愈失真以及应的愈来愈茫然。
【在此有必要重申,“失真”并不是“失实”,反而恰恰是“求实”的唯一途径,因为对任何感应物或感应者来说,非此则无从求实。(参阅本卷第六十五章、第八十二章以及第一百零三章等)但,如此看来,“真”与“美”的关系全然不是可以并列共进的关系,反倒是一种反比背离的关系——反比在愈失真者愈有了创生“美”的余地。当然,我不避累赘地强调,这“失真”绝非“失实”,只是使“实”发生了隔阂,使“应”发生了动荡而已。】
因此,可以说,失位为“美”——失而有位,感而无应,美也。
于是,“美”就呈现为这样的状态:
凡是切实的都是不美的;【因为“应”使“感”落实为无趣的“在”。】
凡是不实的亦是不美的;【因为“应”毕竟是“感”的最终标的。】
也许下面的话有些多余,不过还是澄清一下为好:上述所谓的“不美”绝非“丑”的概念,而是“无美无丑”的意谓,因为“丑”不外乎是“美”的组成部分,亦即是“美”的抑扬顿挫的旋律罢了。
【“审美”就是在这个感应属性或精神内核的深隐质地上生发的浅层直观以及显性观审,就此而言,可以说“审美现象”只是“美的本质”之汪洋表面的浪花或涟漪罢了。一般学者的审美之论就漂浮在如是层面上,不过,即便这般浮浪荡漾,惬意之余,也还不免缺失了浅层意义上“美”与“丑”的另一种分别,那就是感应依存或代偿效用的指标性亦即指示性分别。
便是要问,审美活动中何以会有“美”与“丑”的观感?答曰:美丑之间暗藏着依存激励的向度指示差别,就像感觉上的甜、香、臭、苦其实导引着能量多寡和毒害程度之间的代谢取舍一样。
譬如,细腰肥臀的女性优柔之美其实来自于骨盆大小是否有利孕育胎儿的恰当尺寸;虎背熊腰的男性阳刚之美实际渊源于筋骨健硕必然有助种间种内的生存竞争;鲜花绽放流露的是植物正当繁殖旺盛状态的生机盎然之美;残荷败柳显示的是生命趋向凋零收敛阶段的萎谢颓然之丑;春夏之明媚在于万物复苏;秋冬之萧瑟在于寒霜肃杀……如此而已。可见,一切美学问题不外乎生灭之间,不外乎损益鉴别,不外乎存续照应。】
所谓“切实”就是“应”的实现,汉文中的“切”字有“游刃深于骨”的意味,即是说,“应”比“感”要实在得多、深入得多,它足以抵达元存,从而成就了元存,因此才说“应”落实就是“在”的达成。相形之下,“感”的浮浅是一望可知的,它原本不过是“应”的一贴诱导剂,“应”一旦落实,“感”随即变得乏味可弃,唯有当“应”之无着,“感”才需深化,“美”才会焕发。
显然,说到底,美的实质全在于维系依存。或者说得更形象一些,“美”无非是“感”与“应”之间失位性联系的一种黏合剂。
所以,凡是未及于“应”的“感”都可能呈现为“美感”,而且,感应分裂愈剧者,其感中之美愈丰。
于是,只有处在切实与不实之间者为“美”,或者说,只有处在失真而不失实之间者为“美”——这种情形俨如生命的存在处境:它虽然失离于元存之“真”,却不失于代偿之“实”,从而既体验了美(主观派生之“自然美”),也造化了美(客观实创之“艺术美”)。
【浪漫主义以脱离现实的方式回归现实;现实主义以回归现实的方式脱离现实;故而二者皆有同质的美感。这就好像美女做了妻子,她的美貌必须内秀化为某种渺远的精神,其美才得以永驻;而做情人者,她的貌美即使并不卓著,仅因距之邈远而荡人心魄。
这缘故无非是因了生存的微妙,微妙在“失之嫌轻,执之嫌重”的代偿素质上。即由于生命存在的失位摇摆,感而应之,非生命也;感而不应,无生命也;唯有在感应离异间荡而晃之,生命的危存方能达成。故,艺术之美的确是生存形势的反映,宛如随风放起的风筝,沉重的一端执在自然元存手中,轻飏的一端撒出感应代偿之外,执而悠远,飏而无失,是乃“生存”与“审美”的一线之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