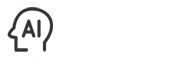《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五章 社会正义
正义——乃是社会结构成长或社会属境代偿在伦理逻辑上的宏大观念体现和综合意向表达。
即作为后衍性生物存在的人类,以自为而不自觉的智质演动方式,在个性残化与群体组合之间所形成的集体内向体验,并借以追求或促进社会结构的滚动扩张和自然发展。由于人类的整体衍存倾向及其总体意识倾向是必然“向善”的,于是“向善的要求”也就倾向于汇集成某种“正义的思潮”向前涌动,“正义”俨然成了一种社会逻辑(而非“个人逻辑”)和社会意志(而非“个人意志”)的风向标,而实际上,“义”是否“正”,全然取决于社会演动的方向是否符合自然演运之规定。
【所以,在把社会结构引向急遽分化的工业时代以前,“正义”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正统”;其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导致马克思首次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宣言,列宁进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高呼“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虽然由于阶级只能在国家结构单元上成立而致国运未消,但它的确预示着“国家构型”的摇撼;而今,当罗尔斯还要在国家调控的体制下探讨“公平的正义”时,诺齐克却证明只有“最弱意义的国家”和“社团分化的社会”才能提供“公平”和“正义”的逻辑基础。】
也就是说,“正义”无非是社会结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逻辑的扩张态(即代偿增益态)伦理衍生物,尽管用狭义的小家子气的(即增益前态)道德准则来衡量的话,它其实从无“正义”可言。
当社会结构单元尚处于从中级社会向晚级社会过渡的前文明状态(如亲缘氏族原始群落)时,“正义”——此刻实在谈不上“义理之正”——就是潜隐在动物种群结构单元中的野蛮竞存和兽性天伦;当社会结构单元进位于“小国寡民”(老子语)的离散状态(如部落、部落联盟、封闭型国家)时,“正义”就在社会结构单元内外以丝毫不讲公平仁义的形式展开:对内以等级分明的欺压道统为社会之“正”,对外以实力较量的掠夺战争为国家之“义”;而当社会结构单元弥漫为全球一体的致密状态(如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形态)时,“正义”将继续在整个人类社会结构中以结构本身不讲公平的方式成就自身。
【所谓“结构本身不讲公平”的“正义”是指这样一种演运之流:在人身依附的专制时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当时社会结构所要求的最大“正义”,即当时要求于为臣者的“忠义”以及要求于为君者的“仁义”其实正是当时社会衍存位相的结构性派生物;在物役使人的异化时代,“带着天生的血痕”的“资本剥削体制”就是现实社会结构所要求的具体“正义”,即现时被赋予“全体人民”的“平等人权”其实正是建立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位相性黏合剂;难怪马克思要对这类欺世盗名的东西大加挞伐,然而,纵使由此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纪性社会正义大实验,却终于不可避免地崩坍于世纪性社会正义大失望之中。
显然,“不公平的正义”(相对于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而言)正是“正义的不公平”,说到底,它们都是出于社会代偿演化结构的自然规定,这种情形就像在高等动物的有机体内,通常只占体重1%~2%的中枢神经组织却必须享有20%左右的血液循环供氧量一样,是无可奈何的自然结构规定,而且,随着结构发育的扩延化、繁密化和动荡化,“正义”的内涵似乎倾向于朝着愈益不公平的境界飞升。】
不过,可怜而糊涂的人类反倒偏偏要在这层境界里大呼“正义”,且真诚地认定“正义”是可以呼之欲出的,的确,人类越来越讲求“正义”大抵恰恰是社会结构发展的需要。质言之,它就是“自由”与“平等”的社会逻辑延伸和民主结构要求,即随着“社会自由化”和“社会平等化”的演进,追求“正义”的动势必将越来越成为社会结构度得以提高的催化要素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质载体的自然演运既表达为物化性状(即实体结构)的分化,同时也表达为道德意识(即虚体属性)的代偿,正是由于这种分化和代偿的一脉并行,才衍生出日益繁多的伦理概念和人道体制,也正是由于这种主观和客观的一体动进,才使得社会逻辑要素在社会变革进程上日益凸显为伦理驱策的唯心动因,以与自然逻辑要素在社会变革进程上日益凸显为知识驱策的唯心动因相吻合——总之,生物晚级社会的自然客观动势终究要借助于人类逻辑集合的主观意志盲动来实现。(可参阅卷二论述逻辑和意志的各有关章节。)】